|
|
楼主 |
发表于 2015-11-10 10:50:25
|
查看全部
地球仪为何不受中国皇帝欢迎?不像中国,欧洲诸国林立,相互之间腾挪的空间并不大,再加上耕地面积的有限,这些都催生了他们对大海之外世界的想象和试探。1798年,拿破仑挥军南下,正式入侵埃及,并打算借由埃及东进,仿亚历山大大帝的方式入侵亚洲:他骑着大象,手里拿着经他个人修订过的古兰经。这一举动除了法国本身的地缘政治考量,其中也暗含着拿破仑个人征服东方的憧憬,他深信“威名只能在东方取得,欧洲太小。”为此,他随身带了大批的科学家、天文学家、土地测量员、哲学家、建筑师、工程师和印刷工等人同去埃及,以便记录下法国启蒙之光初临落后东方的盛况。与之相似的行动也发生在当时快速上升的英国。1792年9月26日,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以补祝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的名义,派出以马戛尔尼为首的800余人的使团前往清朝帝国访问。他们随团带着大量诸如航海望远镜、战舰模型、地球仪、铜炮、火枪等最新技术产品入华,并指望靠它们打动中国皇帝。英国使团此举一定程度上可能受了利玛窦在华经历的影响。利玛窦得以进入晚明宫廷,主要靠三件事物引起万历皇帝注意:世界地图,自鸣钟和欧洲钢琴。万历皇帝喜欢自鸣钟,天天放在身边,世界地图也被放大制成了四个屏风。当时的乾隆皇帝跟万历的兴趣不无相似。1750年,乾隆委托意大利天主会教士郎士宁设计了定时水钟和喷泉装置,以供皇家娱乐,也曾让传教士蒋友仁在圆明园的一座大殿墙上绘制世界地图。但无论万历还是乾隆,他们对此的态度基本都是抱着珍玩而非知识的心态。事实证明,乾隆对西方世界几近于无知,以致他在接见马戛尔尼时,才会问出“英国距离俄罗斯有多远,他们关系是否友好?……意大利和葡萄牙是否距离英国不远,是否向英国朝贡?”等可笑的问题。在《停滞的帝国》一书中,法国学者佩雷菲特将这次会面中的景泰蓝与地球仪视为中英两国的象征,多半是在技术层面上的考量。但依靠技术壮大和获利的英国,不懂得这个古老的国家更看重的不是技术,而是礼节,那些列于回礼中的景泰蓝、丝绸、宣纸,也不仅是古老的工艺品技术,更代表着古老的传统。这个传统即是“天下”传统,是万邦来朝的传统。事实上,在马戛尔尼带来的诸多礼物中,地球仪遭遇了明显的冷淡,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当马戛尔尼炫耀地展示地球仪时,满朝大臣看到"日不落帝国"居然占据了地球仪上那么大块的地方,他们感到的不是解惑,而是愤怒:怎么能把天朝大国画得这么小?在祝春亭、辛磊长篇历史小说《大清商埠》中,也有相似情节。来自东印度公司的英国人麦克举着地球仪,对中国官员念着他已反复排练过的台词:“地球仪比你们中国的地图更准确,更直观,更科学。总商先生你睁大眼睛看仔细,中国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处于世界的中心;中国之外,并不都是野蛮小国,还有文明发达的欧洲各国。所谓天朝上国,惟我独尊,自欺欺人。”最后,这只呈上朝堂的地球仪因为在英国版图上使用了中国皇帝专属的明黄色,引得乾隆皇帝勃然大怒。其中还提到,据内务府历年的反馈,乾隆对地球仪、浑天仪之类的玩意兴趣索然。相对而言,久在中国生活的利玛窦无疑更懂得迎合中国人的心理,在制作世界地图时,他不仅将西方惯常的以大西洋为中心的绘图改为以太平洋为中心,还把零度经线移动,意在使中国处于地图正中的位置。但地球仪对中国世界中心位置的挑战显然比地图要大得多。它的转轴再也不可能掩饰中国只是世界上平常的一部分而已。
罗斯托恩地球仪。尽管如此,在中国人自制的地球仪中,我们还是找到了类似利玛窦那样的地理谎言。观察1800年由中国人制作的、现藏于维也纳的罗斯托恩地球仪(ROSTHORN-GLOBE),人们就可以发现那个地球仪的南北方向被倒了过来,而这只是为了视觉上有一种主人的、直观的、向南看的感觉。近代地球仪的在华命运人们在看待外来事物时,总是习惯性地将它理解为来自外部环境的特殊意味。地球仪一开始被视为珍玩,便是中国原有“天下观”里的朝贡体系的视角。这一视角在19世纪遭遇了全面的冲击,并迅速崩溃。列文森曾将19世纪的中国变革描述为“从天下到国家”的过程,中国一词开始从一个文明空间概念,变成了一个民族国家的疆域概念。在这一过程中,忧心忡忡的中国人不得不去学习那些原先权当珍玩的枪炮,以及各种各样的新知识和新技术,虽然这些事物的面貌已被染上了血腥而耻辱的一面。在一贯被压制,又突然奋起的学习进程中,每种知识面临的命运其实是不同的。枪炮、舰船、工厂等快速发展,但地球仪之类的知识在一个国家的紧急状态中近乎无关紧要,尽管随着国家概念的降临,惯于面对中心的中国民众,不得不被迫面对广阔的四周和海平线。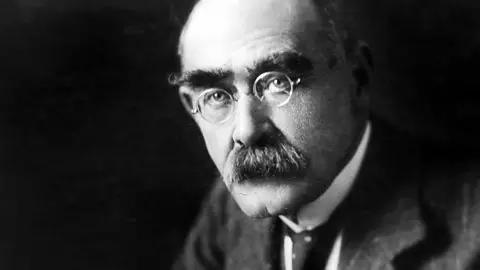
帝国小说家吉卜林。 |
|
 关注公众号
关注公众号 QQ会员群
QQ会员群![]()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080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08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