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楼主 |
发表于 2017-7-13 15:54:35
|
查看全部
德国:为美苏争霸奠基的国际纵火犯(外交胜利,内政失控)
俾斯麦的伟大在于,当普鲁士大众仍沉浸在打败拿破仑的虚假胜利记忆中时,他已明确了维也纳体系必须摧毁的目标且找到了实现的方法。施特雷泽曼的伟大则在于,当德国大众无不对一战结局咬牙切齿之际,他已看出了凡尔赛体系的存在价值,并同样找到了一条新的复兴之路。
年轻时的施特雷泽曼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铁血青年,直到经历了一战的惨痛教训后,他才幡然醒悟,逐步转型成为一名卓尔不群的现实主义战略大师。
1923年1月11日,为了惩戒魏玛共和国和苏俄私下进行外交接触,法国与比利时在没有和英国进行外交沟通的前提下,突然出兵占领了对德国经济至关重要的鲁尔重工业区。联军不仅要通过占领谋求经济补偿,而且图谋将鲁尔区与莱茵区永久性地从德国分裂出去。当时的鲁尔区出产德国73%的煤炭和83%的钢铁。莱茵区则攸关法德双方的国防安全。这两地对德国而言,都是绝对不能放弃的棋筋。
法国人与比利时人的做法激起了轩然大波。德国国内掀起强烈的反抗情绪,极端分子则身体力行地组织起游击队。更有甚者,如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阿道夫·希特勒,已经开始考虑利用外部危机趁机夺取全国政权。德国政府则通过发放补贴的形式支持工人罢工,从而以消极抵抗瓦解法国的入侵行为。而英国则手忙脚乱,既同情法国在战时的巨大损失,又害怕法国过于强大会损害欧洲平衡。至于苏俄,自然是乐于旁观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冲突。
正是在这种空前的大混乱中,施特雷泽曼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复兴战略,并且以其雄辩引起总统的注意,从而在政府业已瘫痪的时刻出任总理,组建新内阁,力挽狂澜。
接到任命后,四十五岁的施特雷泽曼在三十六小时内便完成了组阁任务,这个速度在当时的德国政坛已是神速。
施特雷泽曼很清醒地意识到,问题的关键在于,“关系到我们生死存亡的是莱茵区和鲁尔区必须留在德国”。可是,此时的德国元气未复,实力有限。如果此时和法国摊牌,只能是自找苦吃,正好给对手一个绝佳的报复机会。德国的复兴必将长期延迟。
施特雷泽曼将军事手段放在一边,开始从外交上谋破局。
他向英、美寻求帮助,并与法国进行紧急磋商。可是,当时的英国尽管担忧法国扩张过度,但也很担心德国卷土重来,事情还没有发展到牺牲英法联盟的程度。毕竟一战的巨大阴影还在英国人的心中萦绕。美国同样不急于表态,而乐得坐观欧洲列强冲突。至于法国,断然拒绝和德国谈判。
门,一扇接一扇地关闭。似乎德国已经是穷途末路。但是,施特雷泽曼兵行险道,索性将鲁尔区的消极抵抗也取消了。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消除英美的戒心,同时放大法国的威胁。
反观此时的法国,其环境也很不好。法比联军发现,控制鲁尔的成本太高,收入刚好抵消驻军费用,全无额外盈余。作为这次出兵的一个直接结果,德国马克对美元的汇率直线下跌。在此之前,马克就已经开始贬值,而且速度已经引起经济学家的惊讶。1921年是75∶1, 1922年就跌到400∶1, 1923年初为7000∶1。而法军出兵鲁尔后,这个纪录很快被打破。1923年1月,马克对美元的比值就下跌到18000∶1。 7月1日为160000∶1, 8月1日是1000000∶1。到希特勒发动“啤酒馆暴动”之时,马克对美元更进一步跌到1000000000∶1,此后还跌到天文数字般的25000000000∶1。 马克废纸化当然首先对德国的中产阶层和底层市民造成了灾难性打击,但同时也让德国政府“丧失”了赔款能力,从而让法国骑虎难下。
法国已经升到了顶点,德国也退到了极限。可是,谁也无法取得胜利。假如再这样耗下去,得利的只能是苏俄,以及法、德国内的亲苏革命团体。
此时英国人终于决定出手干涉。
麦克唐纳(James Ramsay MacDonald)入主唐宁街10号后,新内阁决定充当法德调停人。正是靠了英国的介入,鲁尔危机终于以法比联军的撤离而和平解决。在之后的六年里,施特雷泽曼不再担任总理,而专职担任外交部长,以有限的资源参与大国牌局。
他的第一张牌是美国。
将欧洲之外新崛起的美国引入欧洲事务,不仅有助于抵消法国等邻近战胜国对德国的偏见,而且能够从美国得到经济复苏的助力。1924年,施特雷泽曼与美国财政部长道威斯(Charles Gates Dawes)一起启动了“道威斯计划”,这个计划的最大价值不在于减少了德国的年赔款额度,而在于初步形成了德美间的合作关系。此举平衡了欧洲邻国的压力,也让德国获得了经济复苏的推力。
他的第二张牌是苏联。
作为《凡尔赛和约》的另一个孤儿,苏联同样在为打破孤立而努力。在苏联摆出和整个资本主义国家阵营敌对姿态,而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又孤立苏联的情况下,施特雷泽曼搞苏德亲善,最大的困难就在于合作的尺度与目的不易把握。如果真搞成排他性的苏德联盟,必然导致德国被西方世界集体孤立,结果只能说被苏联绑架,因为这个时候德国的力量实在是太过虚弱。所以,施特雷泽曼改善苏德关系的目的仍在于转化出和西方国家交涉的筹码。
有了前面两张牌,施特雷泽曼就开始推进法德和解,甚至表示要在法德和解的基础上,探讨成立欧洲共同体的新道路。
1925年,施特雷泽曼与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法国外长白里安(Aristide Briand),围绕德国的未来地位和相互关系,进行了一次铺垫性的三国外长会谈,初步达成德国以永远放弃对阿尔萨斯—洛林的领土要求,换来英法对德国西部边疆的永久性承认,并且允许德国恢复大国地位。
同年10 月,英、法、德、意、比、波、捷七国在瑞士洛迦诺举行国际会议,最终签署了的《洛迦诺公约》(Locarno Treaties)该公约是1925年欧洲七国(英、法、德、意、比、捷、波)在瑞士洛迦诺举行会议通过的文件总称,是确定一战后欧洲国家边界和领土问题的重要保障,改善了国家间关系。。德国得到了重返国联的机会,而且是在推卸掉共同对付苏联的联盟负担的前提下得到了这个机会。当时,英法希望德国能够承诺在西方国家与苏联发生冲突时参加对苏经济制裁,甚至允许法国军队通过德国领土。对施特雷泽曼而言,苏联是他手中不多的几张牌之一,绝不会轻易放弃。就在洛加诺会议召开的当月,德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一项经济条约,该条约的内容远远超出了一般通商条约的范围。
1926年4 月24 日,德国与苏联又签订为期五年的《苏德友好中立条约》,进一步增强了德国与英法讨价还价的筹码。同年9 月,德国在坚持保留对苏条款的前提下,正式参加国际联盟,并担任了国联理事会的第六个常任理事国。1928年,施特雷泽曼赞同旨在消除战争的《巴黎非战公约》。1929年,他又同美国律师杨格(Owen D.Young)共同制定“杨格计划”(Young Plan),再次修订赔款进度表,并进一步深化德美间的多方位合作。同样是在这一年,白里安和施特雷泽曼开始探讨建立欧洲共同体的可能性,展示了一个新欧洲的愿景。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逐步瓦解以德国为假想敌的英法同盟,进而不动声色地经略东欧,伺机解决德国与波兰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最终通过对东欧的影响,奠定德国在欧洲事务上的影响力。可打可谈,攻防两便。
这一路走来,真是冬日饮水,冷暖自知。施特雷泽曼用了六年时间,给新德国打造了一个全新的外交天地。对一个战败国而言,堪称奇迹。环境如此有利,德国理应是最不应该成为颠覆凡尔赛体系、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家。只可惜,自命伟大的德国人民却在同一个地方连摔了两次!
当年德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激进主义泛滥,宣传过头,欺人的宣传武器变成自欺的精神鸦片。德国人不去想一战末期军队瓦解的事实,不去想如果战争持续的后果是什么,更不去想如果德国战胜可会提出“十四点原则”。他们只一味宣称当年德国是不败而败,是内部出了犹太阴谋集团。热爱和平的德国军民本来可以武斗获胜,却因为这内外勾结的国际阴谋而放下武器,决心用“十四点原则”的精神共造和平。结果,和平没有来,敌人却举起了屠刀。于是,德国就不幸沦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惨境。
今天看来,这个宣传真是漏洞百出,错谬不堪。但是,当年的德国人普遍相信这些宣传,很多外国人也相信。
施特雷泽曼虽然得到外国对手的尊重和理解,却始终无法得到国内政客和大众的理解。他成功地处理了鲁尔危机,却被国人当做窝囊废,他只当了一百零三天的总理,就被人们用不信任投票赶下了台,从而留下了“百日总理”的绰号。时任总统弗里德里希·阿尔贝特(Friedrich Ebert)为此深表惋惜:“你们只要过六个星期就会把赶走总理的理由忘个一干二净。但是,十年后,你们会对自己不负责任的行为深感后悔。”
施特雷泽曼在外交部长任内的举措,也从来没有得到过大众及军队的理解和支持。他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德国的损失,最大幅度地提高了德国的国际地位,但是,却被国内舆论指责为没有争取到更多的利益。
与美国的合作使德国受益匪浅。在“道威斯计划”启动后的五年内,德国支付了十亿美元的赔款,却得到了二十亿美元的贷款。“杨格计划”则带来了更有利的经济环境。可是,激进分子吃饭砸锅,一边享受经济复苏,一边把“杨格计划”当成靶子,肆意发泄非理性的不满,痛骂华尔街金融家剥削德国人民的血汗,却忘了一个基本事实:所谓有用的国家就是有资格被利用的国家,能相互利用然后才能双赢。如果处处只是单方面得利,就永远不会形成合作。
德国通过承认阿尔萨斯与洛林的现状,换来了西部疆域的安全,却同时保留了修正东部国界的自由。这同样是一个重大胜利。可惜,日后的激进主义却利用这一点,急不可耐地要对波兰动武。
同样重要的收获还在于争得了时间,让德国军事力量逐步走出低谷,甚至在德苏合作的基础上开始进行新一轮的军事改革。以当时法德两国的实际力量对比,法国陆军随时能够扼杀这种韬光养晦。问题是,法国人始终没有找到动武的理由,更没有找到争取英美苏三强支持的外交筹码。
与当年的俾斯麦一样,施特雷泽曼在不知不觉间成了新的国际核心人物,德国与美英法苏任何一国的关系,都亲密于四国间任何两国的关系。唯独国内的媒体、政客和日趋骚动的大众,却把他当敌人看待。
1929年10月3日,施特雷泽曼在数小时内连续两次中风后去世,年仅五十一岁。同一个月,美国股市暴跌,引发全球经济危机,德国经济也未能幸免。新的危机面前,德国人很快就彻底忘掉了施特雷泽曼,因为他们自以为已经找到了真正的救星——阿道夫·希特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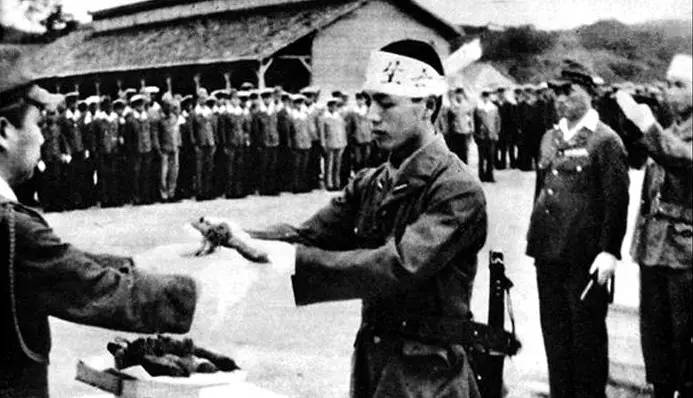 |
|
 关注公众号
关注公众号 QQ会员群
QQ会员群![]()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080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08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