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楼主 |
发表于 2017-8-2 08:29:43
|
查看全部
现况:文言文比例空前,令人担忧
本次“部编本”语文教材出炉,乃是百年来语文教材第七次大换血。文言文再度高歌猛进,篇数占到了小学六年全部课文的30%、中学三年全部课文的51.7%。这个前无古人的高比例,究竟是怎么定下来的,目前尚无权威资料可以说明。
如此大幅度地增加文言文,是否有必要,是否会产生好的效果,笔者是存疑的。
1、复兴“传统文化”,并不意味着从小学就要大量学文言文
比如,支持教科书大量增入古文的人说: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文言文不从娃娃抓起是不行的。
这个理由并不成立。
复兴“传统文化”没有问题。真正有价值的“传统文化”,必然能够与现代文明接榫,比如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之分,就仍值得今人深思,也足以与现代政治文明发生共鸣。[12]
但这并不意味着文言文有必要从娃娃抓起。语文教育的核心目的,是训练学生熟练运用时下的主流语言、文字工具(当然是白话文而非文言文),来自如、自由、自洽地自我表达。这是第一目的,也是最重要的目的。其他任何目的,接榫“传统文化”也好、培养文学才能也罢,只要出现冲突,都须为第一目的让道。小学30%的文言文,初中51.7%的文言文比例,显然会严重干扰到白话文的学习,侵占后者的学习时间(考虑到文言文的学习较为困难,其耗时比例,必然远大于其所占课文的比例)。小学、初中阶段的白话文学习,关系到很多人的一生——当下,国人说话留言写文章,缺乏逻辑词不达意的现象非常严重,大都与小学、初中的白话文学习不合格有关。
他山之石或有参考价值——据2013年的一份统计,台湾“国立编译局”版小学语文教材中,1年级的古诗文比例是0%,2年级是12.9%,3年级是11.1%,4年级是11.1%;至5年级则增至40.74%,6年级增至60.86%。这其中绝大部分是文辞浅显的古诗词,非古诗词的文言文,也多是翻译成白话文后,再呈现给学生。[13]
2、当前的白话文不够成熟,不是让小学生、初中生转而去大量学习文言文的理由
再比如,有一些教育界人士认为:白话文只经历了100年的发展,无法“与文言文的漫长统治相比”,且迭经宏大口号、暴力词汇的污染;白话文缺乏经典作品,“汉语中真正的优秀作品绝大多是用文言文写成的”,“如果一个人的文言文功底很扎实,一定会对他熟练、甚至创造性地使用书面白话文有莫大的帮助。”[14]
这个理由也不成立。
(1)白话文当然有它的问题,也确实是一种尚不算十分成熟的语言。但现实不可逆转,国人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之中,已几乎不再使用文言文。筛选最优秀的白话文作品进入语文教科书,剔除其中所遭受的污染,提升国人的白话文表述水平,才是语文教学当下最应该做的事情。
(2)对成熟的作家而言,扎实的文言文功底,确实可以提升白话文的写作水准。但对小学生、初中生而言,这种“提升”,恐怕多半会是这种面目:
“战书:近闻晓冬兄挑国术之尊威,旌麾太极之初。雷公束手败绩。今在下孙××,隐武多年。终看不下去尔。愿与晓冬兄会猎于京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在下孙××”
(3)文言文也有文言文的问题。台湾当代文学家王鼎均、逻辑学者殷海光,都曾指出,中国古代文言文,常犯逻辑上的致命错误。
比如:“车有两轮,鸟有两翼,是故文武之道不可偏废也”这种话,就毫无逻辑可言——车有两个轮子,鸟有两个翅膀,根本就不能证明“文武之道不可偏废”。遗憾的是,先秦诸子的议论文中,大量使用这种类比推论手法;其中很多被选入语文教科书,且要求学生必须能够背诵。国人今天仍在熟练使用这种手法讨论现实问题,与语文课本的熏陶不无关系。
此外,老子的“道”、孔子的“仁”与“圣人”、宋儒的“理”与“气”……都是涵义极其模糊的概念。这也是中国古代文言文不讲逻辑的一种表现。这一陋习传承至今,语文课本里那些不讲逻辑的文言文,多少也有责任。
略言之,当下中国语文教育的核心目标应该是“让学生学会用白话文自如、自由、自洽地表达”——自如表达,需要掌握足够的词汇和表达技巧;自由表达,需要清除多年沉积的语言污染;自洽表达,需要学会有逻辑地“好好说话”。至于“传统文化”和文学素养,可以有也应该有,但不能干扰乃至破坏核心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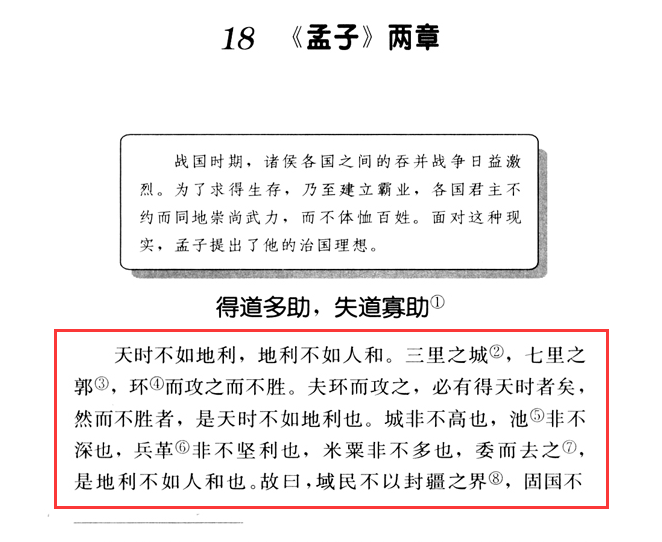 | 原人教版初中三年级下册所选《孟子》。截图所示孟子对“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一结论的论证,可谓毫无逻辑——按孟子的说法:有些得了“天时”的人去攻拥有“地利”的城失败了,就足以说明“天时不如地利”;有些拥有“地利”的城没能守住,就足以说明“地利不如人和”。 |
|
①徐訏,《论文言文的好处》,《论语》半月刊, 1933年第26期。②黄庆生,《一篇很不好教的课文——〈背影〉》,《人民教育》 1951年第3期。③1953年7月号《人民教育》社论《稳步地改进我们的语文教学》之附件:《从“红领巾”的教学谈到语文教学改革问题》。收录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共三册)》,P228-231。④胡乔木,《关于改进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报告》。转引自:潘锋,《建国初期语文教育借用苏联教育经验的历史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⑤王仲杰、轩颖/主编,《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P37。⑥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小学语文教学改革小组,《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 编写新的语文教科书》,《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60年第3期。⑦李良品,《中国语文教材发展史》,重庆出版社,2006,P361。⑧周正逵,《语文教育改革纵横谈》,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P112-113。⑨吴康宁,《“课程内容”的社会学释义》,《教育评论》2000年第5期。⑩周正逵,《语文教育改革纵横谈》,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P113。[11]同上,P118-119。亦可参见:齐浣心,《陈云与古籍整理出版》,中华读书报,2015年9月9日。[12]顾炎武云:“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按顾炎武的逻辑:朱明政权变成满清政权,乃是“亡国”;仁义社会变成丛林社会,则可谓“亡天下”。[13]董雪洁,《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古诗文比较:以苏教版和台湾“国立编译局”版为例》,《世界教育信息》2013年第13期。[14]陈季冰,《强烈建议!中小学语文应至少一半文言文,1930年以后作品原则上不收》,冰川思享库,2017年7月31日。 |
|
 关注公众号
关注公众号 QQ会员群
QQ会员群![]()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080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08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