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国内 |
|
|
| 国民政府 |
| 9月19日,中国驻国际联盟的全权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报告事件,请国联主持公道; |
| 9月19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 |
| 9月21日,施肇基正式向国联提出申诉; |
| 9月23日,中国政府就此事照会美国政府,希望对方“深切关怀”。 |
| 蒋中正事后在1934年10月检讨:中国东北仅名义上归属于国民政府,而军权、政权、财权俨然独立,至少可说非革命势力范围以内之地……胡适等人甚至不惜主张依据日方所提<币原五原则>进行直接交涉。中国中央政府却坚持“不撤兵、不交涉”之原则,致使日本缓和派不能抬头,日本少壮军人气势日张,问题愈陷僵化。 |
| 中国共产党 |
| 中共借由国民政府抗日期间攻城掠地,扩充红军形成地方割据,在长江流域建立了闽西、赣南、湘鄂、鄂豫皖、湘鄂西、闽浙赣等主要根据地,对抗国民政府的游击区域进一步扩大成124县以上[14]。 |
| 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谴责日军侵略,同日,中共中央代总书记王明发表“武装保卫苏联”的讲话。 |
| 9月2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提出组织东北游击抗日(后形成东北抗日联军,即抗联)。 |
| 12月6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北大南下示威团由中央大学集结出发,沿途散发“被压迫民众团结起来”、“全国无产阶级暴动起来”、“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等传单,行经成贤街浮桥时打伤警官2名,警员7名,宪兵1名。11日,中共带领北大南下示威团继续发动示威暴动,并拿出“打倒国民政府”、“工农兵联合起来”、“争取反帝及一切自由”、“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各类油印传单或标语。 |
| 12月15日,北大南下示威团手执红旗直捣国民政府外交部,数名职员不来及逃出遭殴打成重伤;一部份学生约200名左臂䌸红布赴中央党部,以木棍击昏陈铭枢并绑架蔡元培,党部卫士鸣枪示警营救追回,由于蔡元培年事已高又遭胁持拖行半公里,手臂红肿,头部亦受击伤送医。 |
| 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 |
| 在九一八事发当时,乃是张学良亲自下令不抵抗,而蒋介石迟至9月19日到达南昌后,晚间九点至十点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消息。张学良事后自己也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 |
| 荣臻,九月十八日深夜:(节录) |
| 得知日军袭击北大营,当即向北平张副司令以电话报告,并请应付办法。当经奉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故转告第七旅王以哲旅长,令不抵抗......彼时,又接报告,知工业区迫击炮厂、火药厂,均被日军袭击。当时朱光沐、王以哲等,又以电话向张副司令报告,奉谕,仍不抵抗...... |
| 张学良,九月十九日下午: |
| 昨日接到沈电,惊悉中日冲突事件,惟东北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由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 |
| 张学良在战后曾解释:“当时我没想到日军会那么蛮干,我以为他们绝不会这样做。我觉得日本是要以这种军事行动来挑拨我们,因此我下令不要抵抗。我希望和平解决这个事件……后来国民对我的不抵抗有所责难,对这我不能接受。但如果责备我未能看穿日本的阴谋,我承认我有责任。”“从前许多学者研究认为是国民政府指示不抵抗,但其实国民政府的指示是‘相应处理’,‘相应处理’意思是看情况自己去办,等于中央不负责的。因此不能将九一八事变没抵抗的责任推给国民政府。我因为不希望扩大事件,所以采取不抵抗政策。……” |
| 另外,据何柱国旅长回忆,9月12日,蒋在河北石家庄召见张学良时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但空口无凭,至今也没有证据显示蒋曾与张在石家庄会面以及说过此话。[2]1947年,冯玉祥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当中,更是铁口咬定,九一八事变张学良的不抵抗决定,只是在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但张学良在重获自由后,还坚决否认有人说他曾把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电文随时放在身边的说法,说这是“瞎说,瞎说,根本没有这种事情”。根据蒋介石的日记,则否定了张、蒋在河北会面,因为按照蒋介石日记,9月12日蒋介石正在去武汉的船上。另外,关于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回忆“九一八事件当晚,蒋介石曾十多次电函张学良不准抵抗”的说法也没有根据,因为当时蒋介石正在坐船从南京到南昌去指挥剿共的途中,通过蒋介石的日记,也不能证明蒋当晚知道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并且至今并未找到蒋给张发的不抵抗指令的电报,同时郭维城1934才加入东北军。 |
| 尽管日本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衅,张学良在接到蒋介石8月16日电报指令后,于9月6日致电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
| 在1991年其重获自由后,张学良在各种场合多次承认九一八事变当中的“不抵抗”决策完全是其一人所决定,中央政府不应该承担责任。[19]张学良1990年接受日本公共电视台NHK采访时,表示他当时认为“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战争不合乎日本政府的利益,日本政府应会约束关东军”。“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国民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
| 总之,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落下了“不抵抗将军”的评价。由于张学良的不抵抗,日本关东军随后发动了侵占中国东北的战争,以1万余人进攻有14万人中国东北军,并在短短半年内占领东北三省。 |
| 自从东北军守锦州开始,先后无数次向中央提出弹药、人员、资金方面的支援,结果中央政府一方面坚决要求东北军抵抗,另一方面却分文不拔,东北军将领认为中央政府这样做,是要将东北军置于死地,以借日本人之手消灭奉系军阀的势力。其中,东北军将领荣臻厉词批评道:“中央不拨一分粮饷,不发一枪一弹,只在发命抗敌,显然有意徒令东北军牺牲,故置东北军于死地”。当时的行政院长孙科由于从财政部得不到任何增援东北军的资金,辞职下台。继任的汪精卫亦只能一面责令东北军抵抗,另一面分文不出,致使他的抗日要求被张学良婉拒。而另一方面,汪的积极抗日主张也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路线完全相左,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愤而辞职出洋。 |
| 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 |
9月22日,蒋介石向全国人民宣称:“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之态度,静待国际公理之判断。”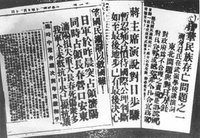 |
当时报刊对918事件的有关报道 |
| 蒋介石当时以“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为原则,以先消除共产党的反对势力分裂主张,再集结力量对抗日本军等外来势力为方针。近期通过蒋介石日记的解密,根据民国史学家杨天石先生的研究,在北伐战争时期,曾在日本留学并熟知日本军力的蒋介石,就有“三月亡国”之论,认为中日国力悬殊,一旦开战,中国沿海地区就会陷入日军之手。日军于1928年出兵济南,制造“五三惨案”,北伐军对日妥协,刻意避开日军,绕道北上,蒋在5月3日日记中写道:“身受之耻,以五三为第一,倭寇与中华民族结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蒋在5月10日的日记里,第一次亲笔写下“不抵抗主义”,但从此之后,蒋介石的日记均以“雪耻”开头。 |
| 另外,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19日,蒋在日记里写道:“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刻接报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有占领牛庄等处。是其欲乘粤逆叛变之时,内部分裂,而侵略东省矣。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而况天灾匪祸相逼而来之时乎?余所恃者惟一片爱国心。此时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耳。” |
| 9月20日记写道:“雪耻,人定胜天。日本侵略东省,是已成之事,无法补救。如我国内能从此团结一致,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故对内部当谋团结也。因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以后,心神哀痛,如丧考妣。苟为我祖我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省永无人格矣。小子勉之。内乱平定不遑,故对外交太不注意,卧薪尝胆,教养生聚,忍辱负重,是我今日之事也。上午与敬之、真如、天翼协商,下午从南昌出发回京。” |
| 9月21日:“雪耻,人定胜天。团结内部,统一中国,抵御倭寇,注重外交,振作精神,唤醒国民,还我东省。下午二时到京,约会干部。余主张:日本占领东省事,先提(交)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一面则团结内部,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对广东,以诚挚求其合作。一、令粤方觉悟,速来南京加入政府。二、南京中央干部均可退让,只要粤方能负统一之责,来南京改组政府。三、胡、汪、蒋合作均可。” |
| 9月22日:“雪耻,人定胜天。上午到市党员大会,余讲至‘国存与存,国亡与亡’之句,有一人讥为‘言过其实’一语。余心为之碎。由此可知,人心已死,国亡无日,哀痛之至,抛碎茶杯,撕破倭本,不觉失态。余复言:我在日本炮火之中不止一次。倭寇在济南炮击机射,余实倭炮中遗留不死之身,决非夸词耳,乃益悲愤。因知爱国者多,而亡国者少,国事犹可为也。下午请稚辉、季陶详述余之怀抱与感想,要胡、汪合作,余交出政权之意。悲戚痛楚,欲哭无泪,哀丧未有如此之甚也。” |
| 9月23日:“雪耻。人定胜天。昨日国际联盟会决议,中日两国停止战时行动,双方军队退回原防,听候联盟会派委员查察裁判。此实为一外交之转机,亦对内统一之机。如天果不亡中国,则此次外交当不致失败也。汉卿派万福麟来京要求外交早日解决,所以官长之财产与东北之痛苦为念,闻之心痛。粤方勾结倭寇以召外侮,图谋推倒中央为快,东北又为一部分之利害急谋解决,不问国际地位与国际形势,以及将来单独讲和之丧辱。呜呼,外侮既急,国内政客官僚非卖国即畏敌,如此民族不亡何待,此次国际联盟既出面干涉,如我国内不能一致对外,则中国从此无人格矣,忧焚无已。晚与万福麟详谈外交形势与东三省地位,与其单独交涉而签丧土辱国之约,急求速了,不如委之国际仲裁,尚有根本胜利之望。否则亦不惜与倭寇一战,以决存亡也。” |
| 9月26日:“雪耻,人定胜天。闻暴日不接受国际联盟通知,并主张中日直接交涉,而国联态度因之转化,从此暴日势焰更张。如果直接交涉或地方交涉,则必无良果。我不能任其枭(嚣)张,决与之死战,以定最后之存亡。与其不战而亡,不如战亡,以存我中华民族之人格。故决心移首都与西北,集中主力于陇海路也。” |
| 民国史学家杨天石认为,蒋介石无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但他虽然对东北领土的沦陷痛心疾首,并也存在团结一致、对日决战、宁死战不苟活的理想,并且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日记中多次提到拒绝与日本和谈,但由于当时中国形势复杂,蒋介石又严重低估了中国人民的抵抗能力,蒋介石实际上的所作所为与他在日记当中的表达的爱国激情有较大差距,可看出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的复杂历史背景。(参见杨天石著作《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同时,蒋介石对日本人的痛恨也无时无刻不跃然纸上,如九一八事变后,蒋曾经与日本方面交涉,他在日记中愤恨的写道:“见日本代表,感想无穷。始见之如和柔,一与之接近,则狡狯之色,轻侮之行,立现无余。欧美各国代表,皆可亲可爱,未有如日本之恶劣也。可知倭奴怕凶而不知礼义,东方之文化皆被倭奴摧残矣。” |
|
| 国内舆论 |
| 九一八事变,东北全境陷落,全国哗然。国人对于张学良“不抵抗”也颇为不满。迨热河失守后,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全国震惊之后”一文,认为热河失守,张学良罪责难逃。胡适毫不客气地指出:“张学良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地质学家丁文江也在同期《独立评论》发表了“给张学良的公开信”,批评张学良既无指挥能力,又不亲赴前线督师,但却恋权不放,陷东北百姓于水火,贻误国家。 |
| 当时,在广东另立中央的汪精卫严厉谴责蒋介石丢失东北,并要求其下野。不久,蒋介石宣布下野负责。汪精卫与孙科等粤系国民党领袖入主南京中央政府。 |
|
| 民间对日宣战运动 |
| 东北抗日联军 |
|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开始大规模入侵东北地区,各地民众及驻军纷纷奋起抵抗,较著名的有如国民政府黑龙江代省主席马占山将军率领的江桥抗战(1931年11月3日~19日)。惜由于各自为政,遭到日军一一肃清,东北三省遂于民国二十一年初全部沦陷。 |
| 游行示威 |
| 9月28日,北平20万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要求对日宣战,收复失地。 |
| 9月28日,南京、上海的二千多学生请愿,冲击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长王正廷被学生打伤,被迫辞职。 |
| 12月,学生运动达到高潮,要求立即“对日宣战”,北平、济南学生占领车站,瘫痪马路交通,上海市长张群遭群众包围,上海市区戒严。5日,“国际联盟”中国代表施肇基、外交部长顾维钧遭到华侨、民众殴打侮辱请辞。广东、浙江、山西教育厅长,北京、中央、中山大学校长,相继被迫请辞。国民政府中枢机关、行政院、中央党部遭到罢课学生瘫痪,人员几无办事之地。15日,蔡元培与行政院副院长陈铭枢在会见学运代表时,遭到学生批斗殴辱[20]。 |
| 1931年7月,由于万宝山事件,日本煽动朝鲜排华反华,中国国内再次爆发抵制日货运动;九一八事变后,运动愈演愈烈。 |
|
| 日本政府 |
| 内阁不扩大方针 |
| 1931年9月19日,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南次郎陆军大臣强调这是关东军的自卫行动,但是币原喜重郎外务大臣(男爵)怀疑这是关东军的阴谋,并且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次事端。9月24日,内阁会议决定了“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 |
| 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 |
| 12月11日,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次日,犬养毅任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荒木贞夫任陆军大臣。 |
| 五一五事件 |
| 1932年3月12日,犬养毅内阁作出决定“满蒙是从中国本土分离独立的统治地域,今后,(日本将)帮助其建立国家体制。”事实上,日本政府在这次事件上被动地被独断专行的关东军制约。(同年日本爆发五一五事件,犬养毅被暗杀。) |
|
| 国际社会 |
| 国际联盟及李顿调查团 |
| 国际联盟派出调查团调查事变始末。1932年10月2日,该调查团发表李顿报告,指出日本发动的事变是侵略中国的行为。由于国联拒绝承认满洲国为独立国家,令日本撤出国联。调查团在事变后一年多后才发表报告,诚然是为时已晚—日本不理会国联的谴责,继续侵略行动。 |
|
| 美国 |
| 1932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亨利·史汀生向日本和中国发表照会,宣布日本对满洲的侵略是对中国领土内政的干涉,违反了巴黎非战公约,因此美国政府对此不予承认。这被称为“史汀生主义”。中国和当时欧洲各国对此都普遍表示赞同,但是日本却无视这一通告。 |
 关注公众号
关注公众号 QQ会员群
QQ会员群![]()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080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080号